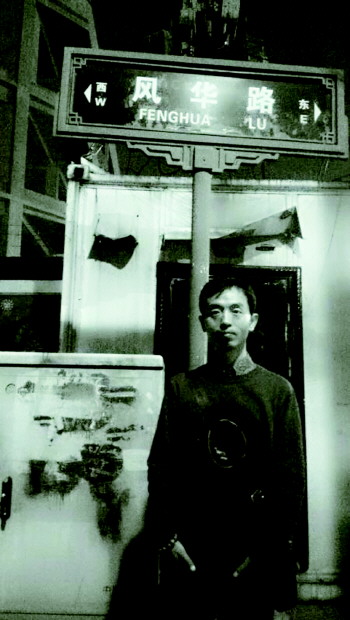邵风华——
写作就是头顶上的星空
本报记者李金金
2016年06月17日 来源:黄三角早报

【PDF版】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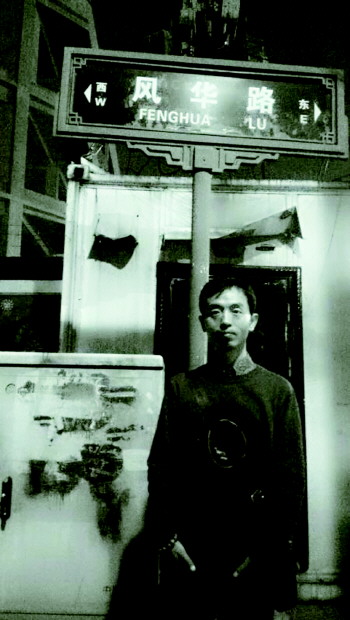
邵风华。
他追求最本真的自己
2002年之前,邵风华一直默默待在小城河口。除了很少的几个朋友,没有人知道他在写诗。更少有人知道他从小就在练字。他在大学时期曾经痴迷过绘画,在那在风云激荡的大学时代,他和同学经常一起骑一辆破自行车穿行在通往书店、博物馆、各种书展的街巷中。也曾经为了省钱,他们爬火车去曲阜的孔林写生,
那时他一直希望自己是一个隐身于周遭环境的人,做最本真的自己。2002年之前,除了身边的三两旧友,很少与其它的写作者发生交集。
邵风华最崇敬的人是塞林格、陶渊明,息交绝游,做一个隐逸之士。每天看着日出日落,倾听风吹过树林。在幽深的飘着花香的小径散步,手里拿着一本书,一本字帖,或一本画册,累了就坐在青石上,在鸟鸣声中一页页翻看。
有一年,邵风华与诗人、评论家胡少卿通电话,这个在北大读了10年书的家伙说他是一个虚无主义者,邵风华连说彼此彼此。人生寄一世,奄忽若飚尘,没有那么多伟大的事业等着他们去做。他们与这个世界发生关系的最好方式,无非就是做一个本真的自己。
但在邵风华的骨子里,仍然汹涌着不可抑止的激情,对生活,对友谊,以及人世之爱。
大约10年前,作家李苇自广州一路北上,曾来东营住过几天,临行前握着邵风华的手说:“我终于理解了你在东营的孤独。”这孤独于邵风华来说,有时是一种滋养,有时是一种伤害,而最终,它只是一种存在的方式。
他感谢那些从各地来东营相聚的朋友,每当他们到来,邵风华都在心里暗暗地说,东营,它知不知有多少优秀的诗人正走在它的街道上。
他曾是一个文学少年
回忆邵风华的写作生涯,算是开始得较早。初一时他开始写小说,初二开始写诗。那是遥远的80年代,又因为就读于偏远的乡镇中学,没有地方可以买书,只能用攒下的零钱偷偷从出版社邮寄。
他从高一开始在《少年文艺》、《语文报》、《诗歌报》等报刊发表小说、诗歌和评论文字。并与朋友一起创办文学社,编辑社团刊物,在学校举办文学讲座。
诗人普珉在一篇文章中说,“邵风华曾是一个文学少年”,原因即在此。
从2002年开始,邵风华移居东营,逐渐与本地的作者有了越来越多的联系。几个人一起策划出版作品集,举办诗歌朗诵,他想用自己和朋友们的努力使这座城市具有更多的诗意。那时的他们是非常快乐的。
在邵风华看来,人生就是一个不断舍弃的过程。只有舍弃,才能拥有真正的自己。所以在他的生活和写作中,舍弃了很多,也收获了很多。
梭罗说,多余的财富只能够买多余的东西,人们灵魂需要的东西,是不需要花钱买的。对一个写作者来说,还有什么是比写作和阅读更幸福的事情呢?
他的生活方式是写作和阅读
在写作上,他是一个题材论的反对者。对于写作者来说,真正的题材只有一个:人性。这个城市的绝大多数写作者难以写出好的诗歌作品,除了才华与阅读的局限之外,有一个很大的原因就是题材的局限,要么局限于“黄河口”,要么局限于“油田”。文学的使命不是讴歌,而是反思、质疑与对人性的诘问。如果它映照出一个时代的精神状况,不是你去追踪、吟唱和摹写,而是时代在个体的内心深处的刻骨印痕。
写作需要灵感,即便小说写作也是如此,何况诗歌。诗歌是神秘的,它的到来犹如神启。诗歌的技术可以练习,但它真正让人怦然心动的部分,必定是诗神的眷顾。写诗不是命题作文。一个不承认灵感的写作者,肯定是平庸的写作者。有的人热衷于参加各种征文和评奖,在网上搜集征文方的资料,然后像写论说文或说明文一样把这些材料罗列,再加上几句感喟成篇。邵风华认为,他们离诗歌太远了。
对邵风华来说,写作和阅读就是他的生活方式,也是他存在的方式,以此获得的快乐,是文学对他的最高褒奖。“我写故我在”这是一个写作者的伦理,类似于康德所说的“头顶上的星空”。写作是对心灵的探寻,远离尘世的纷扰。文学之所以还会有前途,就是由于它以独有的方式表达了人类的心灵和情感。这同时也是一切艺术形式的根本所在。

本稿件所含文字、图片和音视频资料,版权均属黄三角早报所有,任何媒体、网站或个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,违者将依法追究责任。